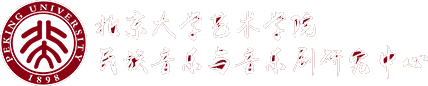中国音乐剧:在歌剧和戏曲之间穿越而过 ——音乐剧本土化研究札记之一
深刻困扰着音乐剧创作界和研究界的最常见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看待音乐剧与歌剧和中国戏曲的关系。
现在公认的一个基本事实是,音乐剧是现代都市文化中一个独特艺术现象。它以美国音乐剧《演艺船》(1927)为自我类型化确立的标志,经历了《波吉与贝丝》(1935)、《俄克拉荷马》(1943)、《南太平洋》(1949)和五、六十年代的《西区的故事》(1957)、《音乐之声》(1959)、《屋顶上的小提琴手》(1964)等一大批百老汇经典剧目的积累走向艺术表达的成熟,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猫》(1981)、《歌剧院魅影》(1986)、《悲惨世界》(1987)、《西贡小姐》(1989)等四大名剧为标志,音乐剧艺术达到了鼎盛期。如今美国百老汇和英国伦敦西区,每天都有几十个不同的音乐剧作品同时上演,世界各地的音乐剧从业人员和数以百万计的观众蜂拥而至,使百老汇和伦敦西区成为世界音乐剧的创演中心和产业中心,并由此辐射开去,在世界各大都市遍地开花。据资料显示,英国“四大名剧”之一的《猫》(Cats),自1981年首演至今,已在世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巡演,是戏剧史上巡演时间最长的剧目。到1997年,它在全世界的票房总收入已超过20亿美元。于是,一部名著造就了一代又一代杰出的音乐剧演员,使他们成为各国“追星族”景仰的世界级明星。1995年,为纪念《悲惨世界》(Les Miserables)公演10周年,英国举行了盛大的化妆音乐会,来自世界17个国家的冉·阿让(剧中男主角)扮演者携手登台,高唱那首激动人心的主题曲《你是否听到人民的歌声》,这一轰动世界的艺术盛举,在艺术史上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作为一个新的艺术门类,音乐剧已经成为世界艺术舞台上的强势力量。
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音乐剧属于全世界,也理所当然地属于中国,但它毕竟不是中国的音乐剧。音乐剧要真正地在中国的文化艺术土壤上生根、发芽、成长,并在世界音乐剧史上留下自己的位置,显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与此同时,有一个问题必须受到追问:我们需要如何廓清中国音乐剧自身的美学特点,以确立自身的创作与表演程式。这样的追问是必要的,因为没有哪一种类型的艺术,可以没有自身明确的质的规定而得到大众的认可,得以健康发展。而且获得大众长久的认可与追随。显然,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若非从音乐剧的文化个性、艺术品质、风格演变,以及对当代城市化进程及大众文化消费心理等多层面多维度地进行探讨,不足以说清这一问题。
事实上,关于中国音乐剧的美学特点的争议由来已久。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早期的音乐剧研究,常常将音乐剧与歌剧混为一谈,中国的原创音乐剧,常被认为和轻歌剧没有明显的区别。而在当下的中国学界,还有观点认为中国的音乐剧就是中国戏曲的现代化表现。
我国权威工具书《辞海》,在“歌剧”词条释义中说:“综合音乐、戏剧、诗歌、舞蹈等艺术而以歌唱为主的音乐戏剧形式……有正歌剧、喜歌剧、大歌剧、轻歌剧、乐剧、音乐剧等类型。”它在“音乐剧”词条的释义却仅仅界定为:“美国的一种音乐喜剧。”不再提及音乐剧是“歌剧中的一种”。而从戏剧研究角度看,戏剧是融合了文学、美术、表演、音乐、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通过语言、动作、场景、道具等多种表现手段,把生活中的矛盾冲突集中地再现于舞台之上的艺术形式。因此,戏剧研究者多认为,广义的戏剧包含了话剧、戏曲、歌剧、舞剧、音乐剧等艺术形式。从其名称上看,当今美国人称音乐剧为MUSICAL,以前称为音乐喜剧MUSICAL COMEDY,英国人目前依旧称其为音乐喜剧MUSICAL COMEDY,而法国人则称之为小歌剧OPERETTE,从这些外文名称上可以看到音乐剧早期与歌剧艺术有些许关联,但是随着音乐剧的发展,人们逐步认识到,无论其内质还是其表现,音乐剧都有自己的质的规定性。
音乐剧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门类,首先是由于音乐剧明确以戏剧为主导,强调歌舞的共同叙事功能,其更为重要的一个质的规定性是:音乐剧歌舞叙事的音乐语言,是以现代流行音乐为主要叙事语言。这是音乐剧与歌剧艺术被分为两大艺术门类的重要原因。20世纪初期,源于综艺秀的音乐剧,辅助消费的娱乐目的是其主要功能,直到1927年出现了里程碑意义的音乐剧《演艺船》,以其出色的歌舞叙事能力使人们感受到了别样的戏剧魅力,造成了空前的轰动,连演了572场,开启了音乐剧历史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演艺船》中歌(音乐)、舞(舞蹈)、剧(戏剧)三者的融合,为后来的音乐剧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创作模式,在百老汇树立了近代音乐剧的美学标准,即要求对白、音乐、舞蹈与戏剧表演融为一体。由此可见,音乐虽然是音乐剧的最重要的表现方式,却并不是主导因素。音乐剧是一门高度综合的舞台艺术形式,其本质终究是以歌舞讲故事,一部音乐剧除了要有生动的歌舞,最为重要的是有一个打动人心的故事。剧本乃一剧之本的创作理念对于音乐剧仍然是颠扑不破的艺术准则。国际上至今成功的音乐剧,至少在故事层面上,亦可以大致总结出一个规定性:首先是要有一个优秀的剧本,要有一个合理的戏剧结构,符合戏剧发展原则,如此才能“讲好”故事,这甚至决定一部音乐剧的成败。音乐剧在具备一个合理的戏剧框架后,通过音乐、舞蹈、对白,以及舞美、灯光等多种艺术表现方式呈现出这个故事,合理安排人物、以及戏剧冲突,以多种形式表现人物的情感世界。
二十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音乐界人士在轻歌剧、音乐剧、歌舞剧、戏曲音乐剧等等诸多称谓中无所适从,很大程度是由于音乐剧与歌剧确有很多共通之处,如前文所述,至今法国人仍称音乐剧为小歌剧OPERETTE。有些作品在轻歌剧和音乐剧之间摇摆不定,如《波吉与贝丝》。还有很多学者认为音乐剧就是由轻歌剧发展而来的。在实际的音乐创作中,很多歌剧导演同时也作为音乐剧的导演,一些歌剧演员同进也作为音乐剧演员。但是,音乐剧与歌剧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又是有目共睹的。它们产生的年代相差300余年。因为它们是不同的社会政治、文化、经济背景与艺术思潮的产物,所以它们的艺术风格、结构特征、表现方式及审美诉求等各个方面均有着巨大的差异。
在艺术风格方面,歌剧与音乐剧的差异,可以看成是“神圣化”与“大众化”的差异。歌剧诞生在十六世纪的佛罗伦萨,在“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一群文化艺术界名人热衷恢复古希腊戏剧,力图创造出一种诗歌与音乐相结合的生动艺术,实验的结果是产生了歌剧。歌剧发展了近400年,在其成形之初,就已形成了音乐与歌唱叙事的质的规定性。纵观歌剧的发展历史,它一直是宫廷化、古典化、精英化、舞台呈现追求程式美的艺术体裁。从剧本选材上看,歌剧艺术更为倾向于表达历史神话或经典故事,尤其强调的是,其文本要善于表现歌唱性,如表现才子佳人爱情主题的歌剧《茶花女》。
音乐剧则产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百老汇,它较多受爵士乐、踢踏舞、话剧和含有歌唱的喜剧等通俗艺术形式的影响,这些成为音乐剧广受大众喜爱的重要原因,也造成了音乐剧通俗性、娱乐性等特点。音乐剧天然地具备“草根”特性,是大众文化的产物。
正如德国著名音乐剧史学家鲁狄杰·柏林在其专著《音乐剧》前言中写道的:“在音乐剧一百多年的发展中,它经历了风格各异的形式,很难下一个完整而确切的定义。首先,音乐剧没有单一的音乐风格……;其次,就配器而言,从古典管弦乐队、爵士乐队到摇滚乐队也是变化无穷。因此,要区分音乐剧与其他音乐作品类型并非易事。”音乐剧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凡是符合大众文化审美需求的艺术风格与艺术手段,都是可以纳入音乐剧的应用范畴的。
在结构方式上,歌剧与音乐剧的差异,可以看成是音乐主导与戏剧主导的差异。美国音乐学家克尔曼在《作为戏剧的音乐》中,这样描述音乐在歌剧中的重要性:“歌剧具有自己独立的审美本位,具备自己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它所能企及的戏剧意义、目的和效果只有在音乐的作用中才能获得独特的财富。因此,我们不能把歌剧中的音乐仅仅当作一个二等的、服务性的仆人角色。如果没有音乐――或者说如果音乐不同,一部歌剧的整体性质便会迥然相异,即使这部歌剧的故事情节与另一部歌剧近乎相同。所以,才会有蒙特威尔弟的《奥菲欧》与格鲁克的《奥菲欧》的差异,才会出现威尔弟的《奥泰罗》与罗西尼的《奥泰罗》的高下之分”
歌剧的主体就是音乐,“作曲家就是戏剧家”。音乐是歌剧的绝对主导因素,以音乐推动戏剧的发展,歌剧中人物性格、人物关系、戏剧冲突等均是通过音乐来表现。歌剧的结构方式可分为分曲结构和四幕结构两种,前者中是由一系列自成段落的分曲组成歌剧结构,由十几个至几十个分曲组成,每一个分曲都是一个有头有尾的、结构完整的独立分曲,即为独唱曲、重唱曲和独唱与合唱相结合的歌曲;四幕结构则是十九世纪后由瓦格纳创造的歌剧结构方式,即是由独立分曲扩大到整个一幕。瓦格纳认为:“被称为歌剧的那个艺术样式最大的错误,就在于表现手段(音乐)变成了目的,而目的(戏剧)则变成了手段。”尽管瓦格纳无比强调歌剧中的戏剧性,但是,歌剧的美学依然是音乐叙事、歌唱叙事,以音乐和歌唱为审美的绝对标准。
音乐剧与话剧结构相同,基本是两幕结构。整体布局上,歌与舞的比例没有程式化限制,同时表现出较大的即兴表达空间,比如可以把一段歌唱转换成一段台词表述出来,这种方式在歌剧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音乐剧以戏剧冲突为推动剧情的主要手段。音乐剧剧本要有对生活场景及戏剧细节的具体描写,避免像歌剧强调歌唱感受、舞剧强调肢体感受,它要给观众的是一个故事的整体感受。音乐剧强调戏剧的整体性,在以音乐与舞蹈为主要叙事手段的同时,并不刻意强调与夸张音乐与舞蹈的呈现,而是通过日常语言的对话、抒情叙事兼具的音乐与舞蹈融合协调的推动剧情发展。因此,音乐剧的美学是由戏剧性、音乐性及其舞蹈性共同建构的。
而在表演方式上,歌剧程式规定性与音乐剧的大众化、个性化则有着明显的差异。无论是西方歌剧和是中国歌剧,演唱者均需经过多年声乐技术训练,娴熟掌握歌剧唱法。歌剧唱法不依靠扩音设备,以追求人声的完美、挑战人声歌唱的极限能力为技术衡量标准,使用交响乐队伴奏是传统的美学要求,具有鲜明的程式性规范和成熟的美学原则;中国歌剧自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以西方歌剧美学为基础,虽然在演唱风格、表演风格、舞美风格方面与西方歌剧有很大区别,其质的规定性是一致的。歌剧的演唱强调音色统一,往往沿用一个固定的唱法,其演唱形式包括宣叙调、咏叹调、重唱、对唱、合唱,其演唱方法、声区划分已形成几百年之久。本质上,欣赏歌剧就是为了欣赏歌唱家的演唱,大段的咏叹调与华美的声音的炫技是吸引观众的重要看点。考察歌剧自身形成的历史条件、发展过程与传播途径,无一不显示着它传统的、精英的小众文化属性。
音乐剧的表演美学是贴近生活的,在大众化中追求个性化。音乐剧舞台上,常见到极具个性化与风格化的演唱,强调用真实的、最符合人物性格的声音来塑造角色。音乐剧演唱较多采用流行歌曲的演唱方法,使用电子扩音设备,即使是轻微的叹息、婉转的低吟,或是喃喃自语,都可以通过麦克传至大剧院的每一个角落。音乐剧不以音乐风格的统一为追求,可根据剧中的人物造型、戏剧环境的改变而调整演唱者的声音状态。音乐剧的演唱虽然以流行歌曲的演唱方法为主,但并不排斥西方歌剧唱法或中国民族唱法,也惯常使用RAP、摇滚、爵士等多种演唱方法,在音乐创作与编曲的手法上,增加大量电声乐队的比重。由于音乐剧音乐注重流行性和娱乐性,因此很多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爱好者也可以自如演唱,甚至可以使用方言演唱。
西方许多音乐剧中的唱段广泛流传,登上流行音乐排行榜高位的作品不胜枚举。比如,音乐剧《音乐之声》中的选段《雪绒花》,音乐剧《猫》中的选段《回忆》,音乐剧《艾薇塔》中的选段《阿根廷,别为我哭泣》等,都是传唱甚广的作品,而1999年首演于伦敦,近年来因票房优异被誉为全球第一的音乐剧《妈妈咪啊》,更是由22首盛行于70年代西方国家的流行歌曲贯穿全剧。
国外大学的音乐剧教学培养,绝大多数是放在戏剧的科系下面,如伦敦艺术大学、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伦敦戏剧中心、苏格兰皇家音乐与戏剧学院、密西根大学、纽约大学、印第安纳大学、杨百翰大学等,音乐剧专业都设置在戏剧的教学系列里。从论述中我们可以总结,音乐剧是以戏剧为主导,以歌唱与舞蹈为主要叙事手段的舞台戏剧形式,与以音乐为主导,以歌唱为唯一叙事手段的歌剧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在学科界定上将音乐剧归入戏剧与影视学科目之下,而歌剧艺术被归在音乐学科目之下,如此分类并无不妥之处。
一件事物转移到另一环境中生长发展,会面临着调整本身内在与外在条件的问题。对音乐剧来说,当它传至中国的时候,它必然面对着如何适应浸淫于中国戏曲文化中的观众的问题,它的调整和适应过程,即是它的本土化过程。在音乐剧的中国本土化过程中,有学者认为,“音乐剧本土化”就是“中国戏曲的现代化”。这种带着强烈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色彩的观点,虽然强调了音乐剧在本土化过程中与中国戏曲的密不可分,但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既取消了音乐剧的独特性,又取消了中国戏曲的独特性。
有一点是无庸置疑的,那就是音乐剧的中国本土化确实离不开它对中国戏曲艺术的吸收。音乐剧与中国戏曲在美学原则上的相通之处,为这种吸收提供了便利,从而也为它的本土化提供了通道。中国戏曲,作为传统的戏剧样式,它植根于民间,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它的观众群体要远远大于音乐剧在全世界的观众群体。。它的源流可以上溯到原始歌舞,自优孟衣冠经汉魏与百戏融合,后经隋唐的歌舞大曲、说唱、参军戏,至北宋形成了宋杂剧,然后在元代和明代进入了它的成熟期,在这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它吸收了音乐、舞蹈、文学、诗歌、杂技、武术等不同的民间艺术。其中,作为防身健体手段的武术被纳入戏曲的范畴,最具有说服力,它不仅成为塑造英雄的手段,还进而发展出了武旦的角色类型。中国戏曲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开放性在世界戏剧史上也是罕见的,这构成了它的综合性的美学特征。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舞台艺术,中国戏曲最重要的叙事方式就是歌舞,正如清末学者王国维所说,“戏曲者,以歌舞演故事也”。这一点,与作为歌、舞、剧三者合一的音乐剧是相通的:既相通于它的综合性,也相通于它的歌舞叙事。也就是说,这是音乐剧与中国戏曲进行有机融合的美学基础。
但是无论如何,正如歌剧和音乐剧属于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一样,音乐剧和戏曲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中国音乐剧的本土化,并不能看成是中国戏曲的现代化。音乐剧的本土化解决的“因地制宜”的问题,通过“因地制宜”而“落地生根”,中国戏曲要解决的“与时俱进”的问题,通过“与时俱进”而让人再次“喜闻乐见”。虽然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方案确有重叠之处,但这并不能抹杀这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的差异性。事实上,只有理解并尊重它们的差异性,它们才可能在发展的同时互相借鉴、相互促进,并进而有效地解决各自所面临的“因地制宜”和“与时俱进”的问题。
音乐剧与中国戏曲在美学形态上的不同之处,突出地表现为音乐剧的写实性与中国戏曲的虚拟性的差异。传统的中国戏曲,重“写意”而轻“写实”,重“神似”而轻“形似”:一扬马鞭,便是骑马跃进;一撑竹篙,便是乘风破浪;走一个圆场就意味着已经越过了千山万水。而西方音乐剧则是高度写实的,《猫》中垃圾场便是由铁桶、轮胎等废弃物真正堆积起来的垃圾场,只是根据“猫”的形体的大小在比例上做了些调整,它在舞台上再现了一个“物”的世界。在《西贡小姐》中,在表现美军乘坐直升飞机从西贡撤退的场景时,一架直升飞机从观众头上缓缓降落到舞台上空,它巨大的噪音将混乱与绝望直接有力地传达给观众。虽然《西贡小姐》被认为是在四大名剧中最具有东方性的西方音乐剧,但这种高度写实性在东方的中国舞台上是不可复制的。中国戏曲的表现方式带有强烈的程式性特征。它把生活中的各种现象,人物表演的各种动作,都规范化了,也就是程式化了。除了上面提到的扬鞭、撑篙,还有开门、关门、上楼、下楼的具体程式,还有表达哭笑、惊惧的具体程式。但奇妙的是,在程式化的同时,演员的表演又有相当的自由度。程式化的表演可以使有经验的观众直接了当地进入剧情,或者说,观众的兴趣不再局限于剧情,而在于集中的观赏演员在程式化表演的背后所呈现出来的演技和风格,观赏演员如何通过自己的演技和风格来抒发剧中人物的情感。观众时常意味深长地议论梅派与程派、此演员与彼演员在唱腔、做功上有着怎样不同的神韵。由此,演员的重要性甚至凌架于所有戏剧因素之上,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一个著名演员跳出剧情的一段清唱也能使观众如痴如醉。演员自身的表演成为戏曲的审美核心,明星自身的表演特点甚至成为一个戏曲的表演流派。这种表演方式的美学特征显然与西方的音乐剧有着显著的不同,
了解这些不同,正是为了给音乐剧的本土化寻找方案。中国的本土音乐剧,完全有可能从中国戏曲中吸取充足的营养,给音乐剧打上中国戏曲的美学色彩。举例来说,当中国音乐剧在表现直升飞机从天而降的场景时,通过舞美设计、音乐、布景和演员的配合表演,完全可以让观众深临身其境,完全可以达到西方音乐剧的舞台效果,完全可以表现人物在类似情景中的情感的细微变化。
所有的外来艺术形式,走入中国的文化土壤,与千年积淀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相融合,都面临着一个民族化的问题。什么是民族化?“民族化,实际上应当是指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吸取外来文化的先进成果,以丰富、补充中国文化,在此基础上建设新文化的过程。”西方的电影电视、绘画设计、歌剧话剧等艺术形式从进入中国的那一天,都面临着民族化的问题。音乐剧也同样面临如何民族化的问题。一种不同于西方歌剧、不同于中国传统戏曲,也不同于西方传统音乐剧的中国本土音乐剧,出现在中国当代的艺术舞台上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
用音乐剧讲述中国的故事,不仅是中国当代的都市生活,也包括中国的历史故事、民间传奇、文学经典,这自然是音乐剧本土化在剧情方面的要求。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穿着民族服装、跳着民族舞蹈、讲述中国民间故事的音乐剧,并不意味着音乐剧的本土化的成功——如果这就是民族化的音乐剧的话,那么,民族歌剧、民间歌舞剧,又如何同民族音乐剧区分开来呢?
一部充分“本土化”的音乐剧,必须是一部在西方戏剧美学与中国戏曲美学的结合部穿越而过的音乐剧。“本土化”不等同于中国传统戏曲与西方现代音乐剧的简单相加,要有效规避与区别戏曲中“形体动作程式化”、“人物造型脸谱化”、“演员形象模式化”等传统风格。“本土化”也不等同于民族歌舞加故事的“民族化音乐剧”。中国音乐剧的表演艺术既应是内部与外部的统一体,也应是理智与情感互相交替的统一体。我们既追求“神似”,又要追求“形似”,要做到“形神兼备”,“情动于衷而形于外”。优秀的表演艺术应该是体验与体现、心灵与形体、感情与理智完美结合的统一体,中国音乐剧应该能够准确而艺术地表现人物形象的外部形体动作,更应该艺术而准确地表现人物的精神生活,即符合音乐剧的现代审美原则,又符合当代中国观众的审美诉求。
音乐剧是一门兼具时代性、都市性、商业性的舞台艺术形式,具有鲜明的大众文化属性,通过戏剧、音乐、舞蹈三大叙事手段,结合多媒体技术、舞台美术共同彰显戏剧魅力。在音乐剧本土化的探索过程中,应该对中西方舞台艺术传统、现代文化环境与艺术发展变化等各个方面进行充分的认知,并在本土化实践中,把握好对音乐剧与民族化、戏曲化的借鉴与汲取的分寸,建构中国音乐剧自身的美学体系。显然,我们还只是刚刚起步。
作者:周映辰,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音乐剧导演。
周小川、肖梦等:《音乐剧之旅》,北京:新世纪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
《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50页。
《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50页
周映辰:《探究音乐剧的学科属性》,《人民音乐》,2015年第3期。
【德】鲁狄杰·柏林:《音乐剧》(前言),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
转引自杨燕迪:《歌剧的真谛:以音乐承载戏剧——评克尔曼的《作为戏剧的歌剧》,《音乐艺术》,2000年1期。
转引自杨燕迪:《歌剧的真谛:以音乐承载戏剧——评克尔曼的《作为戏剧的歌剧》,《音乐艺术》,2000年1期。
瓦格纳:《戏剧与歌剧》。转引自文硕:《中国近代音乐剧史》(下),北京:西苑出版社,2012年版,第342页。
其中,作为防身健体手段的武术被纳入戏曲的范畴,最具有说服力:它不仅成为塑造英雄人物的手段,而且还由此发展出了武生、武旦这一角色类型。武旦作为旦行的一种,它的出现,甚至起到了挽救昆曲的作用:昆剧中本无武旦这一行,清代中期以后,因为剧种的衰弱,昆班吸收了京剧中的武戏,武旦这一行当应时而生,昆剧也暂时避免了被边缘化的命运。
它的“东方性”是指在内容上它表现的是东方(越南)女人与西方男人的爱情故事,在演员的使用上女主角使用了菲律宾女演员 Lea Salonga,她的甜美清脆的声音极具东方色彩,她也是后来给迪斯尼的《木兰》中配唱的演员。当然,就音乐剧的主题而言,它其实更隐蔽地表现在“东方主义”的心态:东方女子被西方征服者玩弄并最终被抛弃,而女子还为之殉情的悲惨命运。剧中把东方女子塑造成了一个一心爱情至上,甘愿为之付出一切的形象,却在最后的结局中以殉情来结束悲惨的人物命运。
何遒欣:《多义的“民族化”》,见彭永启主编《音乐研究文集——沈阳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成立20周年暨音乐研究室成立55周年》,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页。
- 上一篇:北大国际音乐剧大师班拉开帷幕
- 下一篇:周映辰:音乐剧音乐的风格属性和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