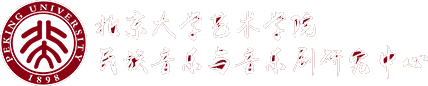周映辰:音乐剧中的故事
圣诞节临近,北京地冻天寒,但娱乐的气氛却愈加浓烈,改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天空中也显出娱乐的气象来。各新闻媒体的娱乐版上,早已提前预告美国百老汇音乐剧《芝加哥》将来京演出,24、25、26日,连演三天,地点就在人民大会堂。
人民大会堂近年成为商演中心,始自陈凯歌和张艺谋。陈氏的《荆轲刺秦王》和张氏的《英雄》,首映式就在人民大会堂。两部电影讲的都是刺杀秦王的故事,刺与被刺的都是英雄。陈凯歌当年面对媒体的质疑,犹抱琵琶半遮面,说在此举办首映式是日本投资方的意思。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日本投资方为何要选择人大会堂呢?这使人想起陈凯歌对“妥协”二字绝妙解释:妥当协商(1)。到了张艺谋,琵琶都懒得抱了,而是大张旗鼓:在人大会堂三层的金色大厅,200名全副武装的“秦军”将士面对北京各大媒体,高喊“风、风、风”,“大风、大风、大风”。看过影片的都知道,秦王卫士就是喊着“风”和“大风”——我至今无法弄清这两句“军令”在影片中的意义,为什么一会儿是“风”,一会儿是“大风”——将李连杰扮演的英雄射成蜂窝状的;现场张贴的巨幅标语上赫然写着“为中国电影加油,为出征奥斯卡助威”(2)。当时就有人议论,走着瞧吧,奥斯卡落选回来,张艺谋肯定会说,奥斯卡嘛,众多电影节中的一个而已,我的影片主要是给中国人看的。还真给说中了,张艺谋后来果然是这么说的。不过,轮到《十面埋伏》的时候,张艺谋又把这话给忘了,又来了一次大型演出,又来了一个“为出征奥斯卡助威”。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第77届奥斯卡的颁奖典礼正在举行,《十面埋伏》自然又是毫无意外地落选了。我几乎可以保证,张艺谋在给下部影片做宣传的时候,还会说他是奔向奥斯卡的。
有意思的是,如果说陈凯歌和张艺谋是要从人大会堂走向奥斯卡,那么,现在是奥斯卡来到了人大会堂。音乐剧《芝加哥》有舞台版,有电影版,舞台版获的是托尼奖,那是音乐领域的奥斯卡奖,电影版获的是正宗的奥斯卡奖。各大新闻媒体在介绍此剧的时候,都要提到同名电影获得过13项奥斯卡提名,最终获得最佳影片等6项大奖。
12月24日的晚上,在这个西方人的平安夜,在中国的首都北京,人民大会堂镜框式的舞台被布置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式的空间。通常情况下,在同一地点,大幕拉开之际,正是国歌响起之时,但此时响起的却是《爵士春秋》,这是一首因为《芝加哥》而响遍全球的爵士乐的经典曲目。一位黑衣女郎在爵士乐的伴奏下,开门见山地说出了本剧的主题:“各位观众,以下的故事讲述谋杀、贪婪、腐败、暴力、剥削、通奸、背叛,全是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主题。”此时观众得以看到,与舞台垂直方向呈45度角的一个巨大的灯框,它有如用灯光编织成的笼子,将事先出场的在现场演奏的爵士乐队围困在了舞台的中央,使他们成为一个直接面向观众的陪审团,当然,所有的演员也都在这个笼子里演出,演绎着那些“触到我们内心深处的主题”。这样一种舞台布置自然也是主题表达的一部分:剧中人物要么受困于监牢和法律制度,要么受困于贪婪和背叛,名誉和虚荣,他们显然希望现场的观众与他们感同身受。
三个小时之后,当我走出人民大会堂,在凛冽的北风中走向前门地铁站的时候,我对自己说,《芝加哥》确实是音乐剧的经典之作。而对于经典之作,我们应该细加分析。
谈论任何一部音乐剧,都有必要谈到1927年。对于音乐剧的历史来说,1927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这一年的12月27号,由奥斯卡·小哈默斯编剧、作词,由科恩作曲的《演艺船》(Show Boat)在百老汇首演。故事讲述的是生活在沿着密西西比河巡回演出的演艺船上的艺人的生活。剧本第一次书写了当时的种族歧视问题,在当时极具冲击力。剧中的许多歌曲,一直传唱至今,比如我们现在熟悉的《老人河》就出自该剧,是由当时著名黑人男低音歌唱家保罗·罗伯逊演唱的。严肃的主题,曲折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塑造和动人的音乐,使《演艺船》造成了空前的轰动,连演了572场,开启了音乐剧演出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它主要的表现手段,比如歌(音乐)、舞(舞蹈)、剧(戏剧)三者的互动,为后来的音乐剧的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模式。正是因为《演艺船》的成功,百老汇才真正确立了美国的音乐剧生产和演出中心的地位,百老汇(Broadway,意味“宽阔之路”)也才能够从纽约曼哈顿区的一个普通街道的名字,成为艺人心中的“圣地麦加”。在此后的1929年、1936年和1951年,《演艺船》又三次被搬上银幕,将它的故事和音乐传遍世界。
在《演艺船》获得巨大成功的同一年,音乐剧《芝加哥》的第一任编导鲍勃·福斯(Bob Fosse)出生了,而与此同时,在芝加哥发生了一起真实的案件:两个渴望成功的女歌舞演员,在杀死了背叛自己的情人以后,被投入了监狱。因为其中一位当时已经成名,属于“公众人物”,所以此事在社会上反响甚巨。刑事案件因其所包含的戏剧性,历来是剧作家们着重挖掘和发展的故事素材,更何况在这个案件中还包含着美国文学中惯有的主题,比如美国梦(通过个人奋斗获得成功)、背叛(在实现美国梦的途中)、令人毁灭的情欲等等。种种因素碰巧遇到一起,似乎预示着在未来的某日必有一场好戏开演。但这个故事最早并非以音乐剧的形式出现,而是以电影的形式出现。事发的第二年,即1928年,这个故事被搬上了银幕,此后又于1942年再次被搬上银幕。又过了13年,即到了1975年,鲍勃·福斯创作了《芝加哥》的第一个音乐剧版本,延续上演了两年,赢得了巨大的票房。1996年在鲍勃版本的基础上,这个故事由约翰·坎德尔(John Kander)作曲,由弗雷德·艾伯(Fred Ebb)作词,再次改编成了音乐剧,同年,在百老汇演出,获得巨大成功,迄今已经在全世界261个城市演出10000多场,观众超过1200万,票房收入达到六亿美元。在《芝加哥》结束在人民大会堂的演出的第二天,从案件发生,到改编成电影和音乐剧,时间刚好是77年。77年之后,我们现在看到的故事已经与最初的故事有很多的不同。经过几代作家、电影人和音乐家的改编,这个故事本身就像一部精彩绝伦的小说。
那两个歌舞演员,一个被命名为罗克茜,一个被命名为维尔玛,她们当然都是色艺双全的。罗克茜梦想成为音乐剧的女主角,成为一名伟大的歌舞演员。她心中的偶像,就是当时的明星维尔玛。罗克茜由于受了感情的欺骗,一怒之下将自己的情人杀死了。罗克茜对丈夫谎称这是一场冤案,说自己并不认识死者,然后说服自己戴了绿帽子的丈夫,让其重金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但是随后,警察向罗克茜的丈夫出示了各种证据,证实罗克茜与死者确有奸情。丈夫认为罗克茜咎由自取,活该受到惩罚。于是,罗克茜就被丢进了监狱,并在监狱里遇到同为囚犯的维尔玛。维尔玛是因为自己的妹妹与丈夫通奸,而杀掉丈夫而进入监狱的。与罗克茜相比,她带有“自卫性质”的行凶使她作为一个受害者的形象更为明显,因而她能够得到世人甚至包括女监狱长的同情。在监狱长的帮助下,维尔玛频频在各个媒体曝光。维尔玛如果能够被判无罪,她将重返舞台,再次成为媒体的宠儿。
维尔玛对罗克茜的到来深怀戒心,怕她抢了自己的风头,并抢走自己的律师比利。比利是芝加哥最有名的律师,颠倒黑白是他的拿手好戏。他最喜欢替名人打官司,于是,他在办理维尔玛案件的同时,也接手了罗克茜的案子,并利用专栏作家的影响,改写罗克茜的故事,以博取陪审团和公众的同情。罗克茜为了能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甚至决定在狱中怀孕。之后,罗克茜和维尔玛都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被宣布无罪释放。出狱后的罗克茜和维尔玛最终同歌舞演员们一起,站在这个给她们带来了名利,也带来了灾难的舞台上,向台下的观众致意。
大幕拉上的时候,回想一下我们都看到了什么呢?阴谋与爱情,贪婪与竞争,司法的腐败和美国梦的虚无?我觉得观众如同剧中写到的那个戴了绿帽子的丈夫,一会儿替罗克茜担忧,一会儿又觉得她罪有应得,后来又与她共同改写历史真相。这种感受实在不妙,但这可能正是创作者所要求的效果:我们所有人都既是局外人又是局内人,我们和剧中人一起,和剧中的那些扮演群众的爵士乐队一起,共同接受审判。当然,我们此时所接受的已经不是美国司法制度的审判,而是人性的审判。同时接受审判的,肯定还有现代社会的一系列运行机制。
既然音乐剧是音乐、舞蹈和戏剧的有机组合,而且无一例外的都是先有剧本,后有谱曲和编舞,那么剧本的故事的选择就显得非常重要。考察百老汇的音乐剧,我们会发现,从《演艺船》开始,百老汇重要的音乐剧,都与小说或电影存着互动关系。《悲惨世界》是根据雨果的同名小改编的,《窈窕淑女》是根据萧伯纳的小说《卖花女》改编的,1957年首演的具有经典意义的音乐剧《西区的故事》是根据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改编的,《来自拉曼察的人》是根据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改编的。这些音乐剧作品所依据的故事,无疑都是经典故事,早已为世人所知晓,带有某种“原型”的意义。所以观众在欣赏音乐剧的同时,注意力可以集中于演员如何用歌舞来阐释人物的命运。音乐剧的成功,又往往引起电影界的注意,电影再度将音乐剧改编成电影,比如《西区的故事》、《音乐之声》皆是如此。当然,电影《芝加哥》的最新版本也是根据音乐剧改编的。同样一个故事,经过文学、音乐、舞蹈的反复阐释,它自然会深入人心。
我这样说,自然还是为了能给华语音乐剧的制作者以必要的提醒。就在2004年12月24日的晚上,北京还有另外两场演出同时进行,一场在首体,一场在保利剧院。首体上演的是音乐剧《雪狼湖》,主演“胡狼”的是香港歌星张学友;保利剧院上演的是张艺谋执导的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雪狼湖》是我后来补看的,而且是为了和《芝加哥》作对比而有意识补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以前在北大百年礼堂演出时,我就已经看过,并组织部分学生讨论过。而在此之前,我还看了宋祖英主演的音乐剧《赤道雨》,以及王静主演的音乐剧《再别康桥》(3)。国内生产的这几场音乐剧,应该说都引起了媒体的充分关注,《文艺报》等主流报刊还对《赤道雨》做出了非常高的评价。对比《芝加哥》,这些作品所暴露出的问题,确实非常明显。我先把音乐和舞蹈放到一边,还来谈它们的戏剧性,即剧中的故事。剧本乃一剧之本,仅从故事层面来说,它们都带有先天的不足。
《雪狼湖》(4)其实是7年前的作品,7年前已经在香港和新加坡连演49场。媒体对此进行了广泛宣传,以吸引人气。现在,国内投资一场音乐剧,最少需要200万人民币,它意味着必须连演50场方能收回成本。7年前的49场,收回成本应该毫无问题。此次在北京演出,被宣传为7年之后全球巡演的首次演出,看来它是准备要在全球大赚一把。但这个全球到底指的是哪些国家的哪些城市,媒体和购票入场的观众所持的宣传册上并没有说明。是不想说,还是不便说?让人颇费思量。我看了演出之后就想,由当红歌星张学友主演的这个故事,拿到全球去演,别国的观众会感兴趣吗?如果别人不感兴趣,那巨额的投资能否收回还真是让人捏一把汗。
故事讲述的是孤独、寂寞的胡狼,平时以养花为生。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富家小姐宁静雪,然后是卿卿我我,你恩我爱。他们憧憬着有一个只属于两个人的雪狼湖,在湖边过着童话般的爱情生活。有一个一直追求宁静雪的富家少爷,设下套子让胡狼犯错,然后让胡狼走进了监狱。胡狼出狱以后,宁静雪已经神秘死去。胡狼为了能再见宁静雪一面,不顾生死,进入“时间伤口”,让时光倒流,然后胡狼和宁静雪任“时间伤口”闭合,沉寂在湖水中静静守候爱的永恒。正如张学友在剧中唱的,这是一个“神话故事”,在二十一世纪初,由剧作者自己编造的一个神话故事。因为是自己编造的,所以它自然是无源之水。所有的神话的故事,都和现实有某种对应关系,是对现实的寓言性呈现。但在这部剧作中,我们既看不到神话的简洁,又看不到现实的复杂。如果我们说这是新编的童话,似乎更为合适。仅从故事层面上看,我看不出这部音乐剧有什么意义。如果不是人气甚旺的张学友来演,谁又会来欣赏这场音乐剧呢?也就是说,这场音乐剧本身的价值是颇值得怀疑的。
情形与此类似的还有宋祖英主演的《赤道雨》。故事讲述的是人民海军舰艇编队在世纪之交三次跨越海洋,出访世界各国。故事的主线是导弹驱逐舰的舰长潘天雨(吕继宏饰)与旅美华人肖可悦(宋祖英饰)悲观离合的情感历程。“爱是长天阔野,爱是小桥流水,爱是两心相悦,爱是一生无悔”,这个带有汪国真情调的歌词,据说体现了全剧对于爱情的完美诠释。至于剧名,按编剧周振天的说法,赤道雨是一种幸运的符号,“过赤道是中国海军从浅蓝走向深蓝,走向大洋的标志。对于航行在大海上的人来说,能遇到赤道雨是一种幸运。”为什么呢?“因为它变幻莫测,水兵们都把淋到赤道雨作为一种莫大的荣誉。而赤道雨这三个字作用于该剧主人公情感历程时,就象征着当代人对爱情、对人生、对命运的复杂心态和感触。”(5)照此说来,“赤道雨”是这部音乐剧中最主要的意象,如同《演艺船》里的那艘船。但演艺船在剧中的象征意义却是非凡的,它令人想起神话中的方舟,它所呈现人类生活的大寓言。《赤道雨》里倒是有现成的一条船,即那艘巨大的舰艇,但有意思的是,编剧并没有充分利用这条船来展开故事,它的“耀武扬威”也仅仅是在情绪上与主人公的爱国主义精神相通。看完整个故事,你会感到,编导之所以用“赤道雨”为题,无非是为了满足观众的好奇心:什么叫赤道雨?路过赤道时会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发生?从故事和舞蹈的编排角度上说,它好像也只是为了能够有机会展示夏威夷的草裙舞,美国的踢踏舞。这些舞蹈,确实是美国音乐剧中最常见的构成元素,但问题是,这样一种移步换景式的编排方法与主人公的内心世界的表达,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预先设置的爱国主义主题与猎奇式展示美国西洋镜中的生活场景,这两者之间甚至存着互相拆解的关系,由此可见,这部投资数百万元、历经三年打造、前后易稿三十次的音乐剧,在主题的表现上存在着严重的分裂,在故事构造上有很多有待商榷之处。这样的作品当然不可能连演50多场,也就是说,收回成本完全是不可能的。这也就决定了,虽然它可以连演多场,但我们还是可以认为,它的演出是“一次性”的,不可能流传并成为屡演不衰的名剧
如前所说,从真实的案件到小说(或戏剧),再到电影,再到音乐剧,这几乎是百老汇音乐剧的必要流程。这也是一个不断雕琢、使之由璞变玉过程。在这方面,同期上演的《大红灯笼高高高挂》倒是尊重了这个规律,虽然它并非音乐剧。苏童的这部小说(原名《妻妾成群》)先是被改成了电影,妇孺皆知之后,才被改成了芭蕾舞剧。虽然为了适合不同的剧种,情节和人物有所取舍,但基本的故事构架,仍然和小说、电影保持一致。如果哪一天它又被张艺谋改编成了话剧,我相信它依然会有超出投资的足够的票房收入。我记得《大红灯笼高高挂》在北大礼堂演出之后,北大学生对其中的“麻将舞”很感兴趣,说原著中没有。从小说中的一个很小的“动机”发展到音乐剧中的一个重要的“主题”,以及由此相关的各种取舍、发展,或者说“差异性”,都能够引起人们对不同的艺术媒介的思索。这当然都是很有意味的,我想,美国的观众在看《芝加哥》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思考。对市场来说,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卖点”。我现在想问的是,我们的音乐剧创作难道不能从中得到启示吗?
每一种艺术门类都有它自己的“质的规定性”,音乐剧自然也不能例外。国际上至今成功的音乐剧,至少在故事层面上,已经可以大致总结出一个“规定性”。首先是要有一个好故事,这个故事放在电影里是好故事,放在音乐剧里仍是一个好故事。但因为它是音乐剧,所以它最好在选材上适合用音乐剧的形式来表现。
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芝加哥》讲述的故事是歌舞演员的故事:题材本身与音乐剧所要求的“歌”与“舞”是一致的,是一种双向同构的关系,即演员演的就是自己的生活,正是这样一种生活塑造了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有一种“自洽性”。1979年,百老汇推出了一部音乐剧《艾维塔》(Evita)至今仍在世界各地上演。它是音乐剧作曲大王安德鲁·劳埃德·韦伯(Androw Lloyd Webber)来到百老汇以后写出的第一部作品。故事的主人公,少女艾维塔来自阿根廷下层社会,她天生一副金嗓子。为了生计,她在下等酒吧卖唱,后来又成为时装模特和电影演员。美貌、金嗓和名声,使她得以接识了总统庇隆,成为总统夫人并兼任阿根廷的副总统。在政治舞台上,艾维塔也极具表演天赋,在新闻记者的镜头前曾亲吻麻风病患者。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是神话中的灰姑娘故事在现实中的翻版,是当代的世俗神话。仔细打量这个故事,会发现它在很多方面与《芝加哥》非常相似。这样一个故事,改编成音乐剧几乎是水到渠成的。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那首名曲《阿根廷,不要为我哭泣》,就出自这部音乐剧。它一经推出,仅在英国伦敦就连演了2900场,一年后回到百老汇,又连演了1600场。1996年,这部音乐剧被改编成电影,艾维塔由麦当娜扮演,再次引起全球轰动。在我们的本土资源中,是否有这样的天生适合改成音乐剧的故事呢?我认为是有的,比如周旋的故事,阮玲玉的故事,刘三姐的故事。电影《半夜歌声》若改成音乐剧,也是一个很好的故事。歌舞剧《刘三姐》曾被张艺谋看中,搞成了一部大型音乐剧——在这方面,你不能不佩服张艺谋良好的嗅觉。但张艺谋版的这部音乐剧,因为过于铺张,过于依赖桂林的自然环境,而很难在桂林之外的城市上演,也就是说,它更像是一部为当地政府服务的旅游宣传片,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张艺谋自《英雄》以来在好莱坞与主旋律之间左右逢源的习惯性思维。但不管怎么说,这部音乐剧还是提醒我们,从本土的文化资源中是可以“检索”到适合创作音乐剧的故事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只有用歌舞演员的生活来创作音乐剧,才能够出现经典作品。音乐剧《猫》(Cats)可以说是近来少有的杰作,但它在很多方面都不符合音乐剧的创作规范,比如,它几乎没有剧本,只是根据艾略特的诗歌来作为戏剧发展的大纲;它也不注重情节的完整性和尖锐的戏剧冲突,全剧甚至只有一个场景;它也没有明星压阵。所有这些,都类似于异想天开。但是,仔细打量以后,我们会发现,它的构思其实非常完整。它虽然没有完整的故事,但艾略特的诗歌在欧美国家却享有相当高的知名度,相当流行,曾经的精英现在已经成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这样的诗歌以音乐剧的形式推出,自然引人入胜。为了弥补情节上的缺憾,这部音乐剧更多地强化了人物对命运的感悟,有点类似于将中国的汉赋改成了歌剧,类似于将人们耳熟能详的李白的诗歌谱上了新曲。还有一点不能不提,即以动物为主角的音乐剧,在音乐剧市场自然显得别开生面。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猫》的主创人员,被称为音乐剧沙皇的麦金托什(Mackintosh)在《猫》之后创作的下一部音乐剧,就是写歌舞演员生活的《歌剧院幽灵》。幽灵之后,他又投入了新的音乐剧创作,它的名字叫《悲惨世界》。众所周知,它原是维克多·雨果的故事,主题与《芝加哥》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涉及到我们内心的贪婪,我们的罪,当然,还有拯救。它是一个好故事,任何时代都是好故事。
注释:
(1).陈凯歌的原话为:“妥协的具体意思是什么呢?是‘妥当协商’的意思,也是‘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意思。”见《广州日报》2002年7月23日记者对陈凯歌的采访《陈凯歌,笑骂由人》。
(2).英雄首映式于2002年12月14日于人民大会堂举行。见《北京青年报》2002年12月16日相关报道。
(3).《再别康桥》于2001年12月1日至26日在北京人艺小剧场上演,导演陈蔚,作曲周雪石。
(4).据《文艺报》2005年3月17日报道,《雪狼湖》于1997年3月28日在香港红堪体育馆首演,此前已斥资1亿港元。
- 上一篇:周映辰:音乐剧音乐的风格属性和取向
- 下一篇:【专著列表】音乐剧研究现有著作